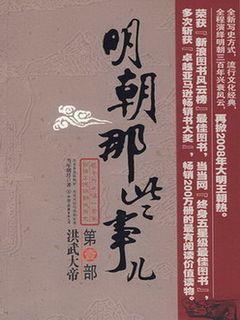- [ 免費 ] 第壹章 童年
- [ 免費 ] 第二章 災難
- [ 免費 ] 第三章 踏上征途
- [ 免費 ] 第四章 就從這裏起步
- [ 免費 ] 第五章 儲蓄資本
- [ 免費 ] 第六章 霸業的開始
- [ 免費 ] 第七章 可怕的對手
- [ 免費 ] 第八章 可怕的陳友諒
- [ 免費 ] 第九章 決戰不可避免
- [ 免費 ] 第十章 等待最好的時機 ...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洪都的奇跡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鄱陽湖!決死戰! ...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下壹個目標,張士誠 ...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復仇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遠征沙漠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建國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胡惟庸案件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掃除壹切腐敗者! ...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空印案郭桓案 ...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最後的名將——藍玉 ...
- [ 免費 ] 第二十壹章 藍玉的覆滅 ...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二章 制度後的秘密 ...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三章 終點,起點:最後 ...
- [ 免費 ] 第二十四章 建文帝:建文帝的 ...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五章 等待中的朱棣:朱 ...
- [ 免費 ] 第二十六章 準備行動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七章 不得不反了! ...
- [ 免費 ] 第二十八章 妳死我活的戰爭 ...
- [ 免費 ] 第二十九章 朱棣的對手 ...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 離勝利只差壹步! ...
- [ 免費 ] 第三十壹章 殉國、疑團、殘暴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章 帝王的煩惱
- [ 免費 ] 第二章 帝王的榮耀
- [ 免費 ] 第三章 帝王的抉擇
- [ 免費 ] 第四章 鄭和之後,再無鄭和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章 縱橫天下
- [ 免費 ] 第六章 天子守國門!
- [ 免費 ] 第七章 逆命者必剪除之!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章 帝王的財產
- [ 免費 ] 第九章 生死相搏
- [ 免費 ] 第十章 最後的秘密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朱高熾的勇氣和疑團 ...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朱瞻基是個好同誌 ...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禍根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土木堡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力挽狂瀾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決斷!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信念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北京保衛戰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朱祁鎮的奮鬥 ...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回家
- [ 免費 ] 第二十壹章 囚徒朱祁鎮 ...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二章 奪門
- [ 免費 ] 第壹章 有冤報冤,有仇報仇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章 隱藏的敵人
- [ 免費 ] 第三章 公道
- [ 免費 ] 第四章 不倫之戀
- [ 免費 ] 第五章 武林大會
- [ 免費 ] 第六章 明君
- [ 免費 ] 第七章 鬥爭,還是隱忍?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章 傳奇就此開始
- [ 免費 ] 第九章 悟道
- [ 免費 ] 第十章 機會終於到來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必殺劉瑾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皇帝的幸福生活 ...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無人知曉的勝利 ...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東山再起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孤軍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奮戰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死亡的陰謀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沈默的較量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終結的歸宿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新的開始
- [ 免費 ] 第壹章 皇帝很脆弱
- [ 免費 ] 第二章 大臣很強悍
- [ 免費 ] 第三章 解脫
- [ 免費 ] 第四章 龍爭虎鬥
- [ 免費 ] 第五章 鋒芒
- [ 免費 ] 第六章 最陰險的敵人
- [ 免費 ] 第七章 徐階的覺醒
- [ 免費 ] 第八章 天下,三人而已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章 致命的疏漏
- [ 免費 ] 第十章 隱藏的精英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勇氣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東南的奇才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天下第壹幕僚 ...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強敵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天才的謀略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戰爭——最後的抉擇 ...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名將的起點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制勝之道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侵略者的末日 ...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英雄的結局
- [ 免費 ] 第二十壹章 曙光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二章 勝利
- [ 免費 ] 第壹章 致命的正義
- [ 免費 ] 第二章 奇怪的人
- [ 免費 ] 第三章 天才的對弈
- [ 免費 ] 第四章 成熟
- [ 免費 ] 第五章 最終的亂戰
- [ 免費 ] 第六章 高拱的成就
- [ 免費 ] 第七章 死鬥
- [ 免費 ] 第八章 陰謀
- [ 免費 ] 第九章 張居正的缺陷
- [ 免費 ] 第十章 敵人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千古,唯此壹人 ...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謎團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野心的起始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明朝的憤怒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兵不厭詐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平壤,血戰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不世出之名將 ...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二次攤牌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勝算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為了忘卻的紀念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章 絕頂的官僚
- [ 免費 ] 第二章 和稀泥的藝術
- [ 免費 ] 第三章 遊戲的開始
- [ 免費 ] 第四章 混戰
- [ 免費 ] 第五章 東林崛起
- [ 免費 ] 第六章 謀殺
- [ 免費 ] 第七章 不起眼的敵人
- [ 免費 ] 第八章 薩爾滸
- [ 免費 ] 第九章 東林黨的實力
- [ 免費 ] 第十章 小人物的奮鬥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強大,無比強大 ...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天才的敵手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壹個監獄看守 ...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毀滅之路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道統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楊漣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殉道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袁崇煥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決心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勝利 結局
- [ 免費 ] 第壹章 皇太極
- [ 免費 ] 第二章 寧遠,決戰
- [ 免費 ] 第三章 疑惑
- [ 免費 ] 第四章 夜半歌聲
- [ 免費 ] 第五章 算賬
- [ 免費 ] 第六章 起復
- [ 免費 ] 第七章 殺人
- [ 免費 ] 第八章 堅持到底的人
- [ 免費 ] 第九章 陰謀
- [ 免費 ] 第十章 鬥爭技術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投降?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純屬偶然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第二個猛人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突圍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壹個文雅的人 ...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孫傳庭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奇跡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天才的計劃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選擇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沒有選擇
- [ 免費 ] 第二十壹章 結束了?
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-AA+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
简
第二十壹章 結束了?
2025-2-12 17:41
結束了嗎?
結束了。
真的結束了嗎?
沒有。
是的,從技術角度講,這篇文章已經結束,我相信,很多人都能看出,它不僅是歷史。
我所述說的,除了歷史,還有很多東西,他們的名字分別叫做:
權力、希望、痛苦、憤怒、猶豫、冷漠、熱情、剛強、軟弱、氣節、度量、孤獨、殘暴、寬恕、忍耐、邪惡、正義、真理、堅持、妥協、善良、忠誠。
足夠多了。
現在我要講述的,是最後壹樣東西,它隱藏在下面的故事裏。
徐宏祖出生的時候,是萬歷十五年。
在這個特定的年份出生,真是緣分。但外面的世界,跟徐宏祖並沒有多大關系,他的老家在江陰,山清水秀,不用搞政治,也不怕被人砍,比較清凈。
當然,清凈歸清凈,在那年頭,要想出人頭地,青史留名,只有壹條路——考試(似乎今天也是)。
徐宏祖不想考試,不想出人頭地,不想青史留名,他只想玩。
按史籍說,是從小就玩,且玩得比較狠、比較特別,不扔沙包,不滾鐵環,只是四處瞎轉悠,遇到山就爬,遇到河就下,人極小,膽子極大。
此外,他極其討厭考試,長大後,讓他去考科舉,死都不去。該情節,放在現在,大致相當於抗拒高考。
這號人,當年跟今天的下場,估計是差不多,被拉回家打壹半死不活,絕無幸免。
然而,徐宏祖的父母沒有打他,非但沒有打他,還告訴他,妳要想玩,就玩吧,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就行。
這種看似驚世駭俗的思想,似乎很不合理,但對徐家人而言,很合理。
對了,應該介紹壹下徐宏祖同誌的家世,雖然他的父母,並非什麽大人物,也沒名氣,但他有壹位祖先,還算是很有名的,當然,不是好名。
在徐宏祖出生前九十年,徐家的壹位先輩進京趕考,路上遇到了壹位同伴,叫做唐寅,又叫唐伯虎。
沒錯,他就是徐經。
後來的事情,之前講過,據說是徐經作弊,結果拉上了唐伯虎,大家壹起完蛋。進士沒考上,連舉人都沒了,所以徐經同誌痛定思痛,對坑害了無數人(主要是他)的科舉制度深惡痛絕,教育子孫,要與這個萬惡的制度決裂,愛考不考,去他娘的。
對這段百年恩怨,徐宏祖是否了解,不清楚,但他會用,那是肯定的。更重要的是,徐家雖說沒有級別,還有點兒錢,所以他決定,索性不考了,出去旅遊。
剛開始,他旅遊的範圍,主要是江浙壹帶,比如紫金山、太湖、普陀山等。後來愈發勇猛,又去了雁蕩山、九華山、黃山、武夷山、廬山等。
但這裏,存在著壹個問題——錢。
旅行家和大俠的區別在於,旅行家是要花錢的,列壹下,大致包括以下費用:交通費、住宿費、導遊費、餐飲費、門票費,如果地方不地道,還有個挨宰費。
我說過,徐家是有錢的,但只是有點兒錢,沒有很多錢,大約也就是個中產階級。按今天的標準,壹年去旅遊壹次,也就夠了,但徐宏祖的旅行日程是:壹年休息壹次。
他除了年底回家照顧父母外,壹年到頭都在外面,但就這麽個搞法,他家竟然還過得去。
原因很簡單,比如交通費,他不坐火車、也不坐汽車(想坐也沒),少數騎馬,多靠步行(騎馬爬山試試)。
住宿費,基本不需要,徐宏祖去的地方,當年大都沒有人去,別說三星級,連孫二娘的黑店都沒有,樹林裏、懸崖上,打個地鋪,也就睡了。
餐飲費,也沒有,我考察過,徐宏祖同誌去的地方,也沒什麽餐館,每次他出發的時候,都是帶著幹糧,而且他很扛餓,據說能扛七八天,至於喝水,山裏面,那都是礦泉水。
門票費也是不用了,當年誰要能在徐宏祖同誌去的地方,設個點收門票,那只能說明,他比徐宏祖還牛,該收。
挨宰費是沒有的,但挨宰是可能的,且比較敞亮,從沒有暗地加價坑錢,都是拿刀,明著來搶。要知道,沒門票的地方,固然沒有奸商,卻很可能有強盜。
據本人考證,徐宏祖最大的花銷,是導遊費用。作為壹個旅行家,徐宏祖很清楚,什麽都能省,這筆錢是不能省的,否則走到半山腰,給妳挖個坑,讓妳鉆個洞,那就休息了。
就這樣,家境並不十分富裕的徐宏祖,穿著儉樸的衣服,沒有隨從,沒有護衛,帶著幹糧,獨自前往名山大川,風餐露宿,不怕吃苦,不怕挨餓,壹年只回壹次家,只為攀登。
從俗世的角度,徐宏祖是個怪人,這人不考功名,不求做官,不成家立業,按很多人的說法,是毀了。
我知道,很多人還會說,這種生活荒謬,是不符合常規的,是不正常的,是缺根弦的,是精神有問題的。
我認為,說這些話的人,是吃飽了,撐的。人只活壹輩子,如何生活,都是自己的事,自己這輩子渾渾噩噩地沒活好,厚著臉皮還來指責別人,有多遠,就去滾多遠。
徐宏祖旅行的唯壹阻力,是他的父母。他的父親去世較早,只剩他的母親無人照料。聖人曾經教導我們:“父母在,不遠遊。”
所以在出發前,徐宏祖總是很猶豫,然而,他的母親找到他,對他說了這樣壹番話:
“男兒誌在四方,當往天地間壹展胸懷!”
就這樣,徐宏祖開始了他偉大的歷程。
他二十歲離家,穿著布衣,沒有政府支持,沒有朋友幫助,獨自壹人,遊歷天下二十余年。他去過的地方,包括湖廣、四川、遼東、西北,簡單地說,大明十三省,全部走遍。
他爬過的山,包括泰山、華山、衡山、嵩山、終南山、峨眉山,簡單地說,妳聽過的,他都去過,妳沒聽過的,他也去過。
此外,黃河、長江、洞庭湖、鄱陽湖、金沙江、漢江,幾乎所有江河湖泊,全部遊歷。
在遊歷的過程中,他曾三次遭遇強盜,被劫去財物,身負刀傷,還由於走進大山,無法找到出路,數次斷糧,幾乎餓死。最懸的壹次,是在西南。
當時,他前往雲貴壹帶。結果走到半路,突然發現交通中斷,住處被當地土著圍困。過了幾天,外面又來了明軍,又開始圍,圍了幾天,就開始打,打了幾天,就開始亂。徐宏祖好歹是見過世面的,跑得快,總算順利脫身。
在旅行的過程中,他還開始記筆記,每天的經歷,他都詳細記錄下來。鑒於他本人除姓名外,還有個號,叫做霞客,所以後來,他的這本筆記,就被稱為《徐霞客遊記》。
崇禎九年(1636),五十歲的徐宏祖決定,再次出遊,這也是他的最後壹次出遊,雖然他自己沒有想到。
正當他考慮出遊方向的時候,壹個和尚找到了他。
這個和尚的法號,叫做靜聞,家住南京。他十分虔誠,非常崇敬雞足山迦葉寺的菩薩,還曾刺破手指,血寫過壹本《法華經》。
雞足山在雲南。
當時的雲南雞足山,算是蠻荒之地,啥也不通,要去,只能走著去。
很明顯,靜聞是個明白人,他知道自己要壹個人去,估計到半路就歇了,必須找壹個同伴。
徐宏祖的名氣,在當時已經很大了,所以他專門找上門來,要跟他壹起走。
對徐宏祖而言,去哪裏,倒是個無所謂的事,就答應了他,兩個人壹起出發了。
他們的路線是這樣的,先從南直隸出發,過湖廣,到廣西,進入四川,最後到達雲貴。
不用到達雲貴,因為到湖廣,就出事了。
走到湖廣湘江(今湖南),沒法走了,兩人坐船準備渡江。
渡到壹半,遇上了強盜。
對徐宏祖而言,從事這種職業的人,他已經遇到好幾次了,但靜聞大師,應該是第壹次。此後的具體細節不太清楚,反正徐宏祖趕跑了強盜,但靜聞在這場風波中受了傷,加上他的體質較弱,剛撐到廣西,就圓寂了。
徐宏祖停了下來,辦理靜聞的後事。
由於路上遭遇強盜,此時,徐宏祖的路費已經不足了,如果繼續往前走,後果難以預料。
所以當地人勸他,放棄前進念頭,回家。
徐宏祖跟靜聞,是素不相識的,說到底,也就是個伴,各有各的想法,靜聞沒打算寫遊記,徐宏祖也沒打算去禮佛,實在沒有什麽交情。而且我還查過,他此前去過雞足山,這次旅行對他而言,並沒有太大的意義。
然而他說,我要繼續前進,去雞足山。
當地人問:為什麽要去。
徐宏祖答:我答應了他,要帶他去雞足山。
可是,他已經去世了。
我帶著他的骨灰去。答應他的事情,我要幫他做到。
徐宏祖出發了,為了壹個逝去者的願望,為了實現自己的承諾,雖然這個逝去者,他並不熟悉。
旅程很艱苦,沒有路費的徐宏祖背著靜聞的骨灰,沒有任何資助,他只能住在荒野,靠野菜幹糧充饑,為了能夠繼續前行,他還當掉了自己所能當掉的東西,只是為了壹個承諾。
就這樣,他按照原定路線,帶著靜聞,翻閱了廣西十萬大山,然後進入四川,越過峨眉山,沿著岷江,到達甘孜松潘。
渡過金沙江,渡過瀾滄江,經過麗江,經過西雙版納,到達雞足山。
在迦葉寺裏,他解開了背上的包裹,拿出了靜聞的骨灰。
到了。
我們到了。
他鄭重地把骨灰埋在了迦葉寺裏,在這裏,他兌現了承諾。
然後,他應該回家了。
但他沒有。
從某個角度講,這是上天對他的恩賜,因為這將是他的最後壹次旅遊,能走多遠,就走多遠吧。
他離開雞足山,又繼續前行,行進半年,翻越了昆侖山,又行進半年,進入藏區,遊歷幾個月後,踏上歸途。
回去沒多久,就病了。
喜歡鍛煉的人,身體應該比較好,天天鍛煉的人(比如運動員),就不壹定好,旅遊也是如此。
估計是長年勞累,徐宏祖終究是病倒了,沒能再次出行。崇禎十四年(1641),病重逝世,年五十四。
他所留下的筆記,據說總共有兩百多萬字,可惜沒有保留下來,剩余的部分,大約幾十萬字,被後人編成《徐霞客遊記》。
在這本書裏,記載了祖國山川的詳細情況,涉及地理、水利、地貌等情況,被譽為十七世紀最偉大的地理學著作,翻譯成幾十國語言,流傳世界。
好的,總結應該出來了,這是壹個偉大的地理學家的故事,他為了研究地理,四處遊歷,為地理學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,是中華民族的驕傲。
是這樣嗎?
不是的。
其實講述這人的故事,只想探討壹個問題,他為何要這樣做。
沒有資助,沒有承認(至少生前沒有),沒有利益,沒有前途,放棄壹切,用壹生的時間,只是為了遊歷?
究竟為了什麽?
我很疑惑,很不解,於是我想起另壹個故事。
新西蘭登山家希拉裏,在登上珠穆朗瑪峰後,經常被記者問壹個問題:
妳為什麽要爬?
他總不回答,於是記者總問,終於有壹次,他答出了壹個讓所有人都無法再問的答案:
因為它(指珠峰),就在那裏!
因為它就在那裏。
其實這個世上很多事,本不需要理由,之所以需要理由,是因為很多人喜歡找抽,抽久了,就需要理由了。
正如徐霞客臨終前,所說的那句話:
“漢代的張騫、唐代的玄奘、元代的耶律楚材,他們都曾遊歷天下,然而,他們都接受了皇帝的命令,受命前往四方。
“我只是個平民,沒有受命,只是穿著布衣,拿著拐杖,穿著草鞋,憑借自己,遊歷天下,故雖死,無憾。”
說完了。
我要講的那樣東西,就在這個故事裏。
我相信,很多人會問,妳講了什麽?
用如此之多的篇幅,講述壹個王朝的興起和衰落,在終結的時候,卻說了這樣壹個故事,妳到底想說什麽?
我重復壹遍,我要講的那樣東西,就在這個故事裏,已經講完了。
所以後面的話,是講給那些不明白的人,明白的人,就不用繼續看。
此前,我講過很多東西,很多興衰起落、很多王侯將相、很多無奈更替、很多風雲變幻,但這件東西,我個人認為,是最重要的。
因為我要告訴妳,所謂千秋霸業,萬古流芳,以及壹切的壹切,只是糞土。先變成糞,再變成土。
現在妳不明白,將來妳會明白,將來不明白,就再等將來,如果壹輩子都不明白,也行。
而最後講述的這件東西,它超越上述的壹切,至少在我看來。
但這件東西,我想了很久,也無法用準確的語言,或是詞句來表達,用最欠揍的話說,是只可意會,不可言傳。
然而,我終究是不欠揍的,在遍閱群書,卻無從開口之後,我終於從壹本不起眼,且無甚價值的讀物上,找到了這句適合的話。
這是壹本臺歷,壹本放在我面前,不知過了多久,卻從未翻過,早已過期的臺歷。
我知道,是上天把這本臺歷放在了我的桌前,它看著幾年來我每天的努力,始終的堅持,它靜靜地、耐心地等待著終結。
它等待著,在即將結束的那壹天,我將翻開這本陪伴我始終,卻始終未曾翻開的臺歷,在上面,有著最後的答案。
我翻開了它,在這本臺歷上,寫著壹句連名人是誰都沒說明白的名人名言。
是的,這就是我想說的,這就是我想通過徐霞客所表達的,足以藐視所有王侯將相,最完美的結束語:
〖成功只有壹個——按照自己的方式,去度過人生。〗
後記
本來沒想寫,但還是寫壹個吧,畢竟那麽多字都寫了。
記得前段時間,去央視《面對面》接受訪談,主持人問我,書寫完的時候,妳有什麽感覺?
其實這個問題,我曾經問過我自己很多次,高興、興奮、沮喪,什麽都有可能。
但當這刻來到的時候,我只感覺沒有感覺。
不是矯情。
怎麽說呢,因為我始終覺得寫這玩意兒,是個小得沒法再小的事。然而,很快有人告訴我,妳的書在暢銷排行榜蹲了幾天、幾月、幾年,然後是幾十萬冊、幾百萬冊,直到某天,某位仁兄很是激動地對我說,改革開放三十年,這本書的發行量,可以排進前十五名。
有意思嗎?說實話,有點兒意思。
雷打不動的還有媒體——報紙、電視臺,從時尚到社會,從休閑到時局,從中央到地方,從中國到外國,借用某位同誌的話,連寵物雜誌都上門找妳。平均壹天幾個訪問,問的問題,也大致雷同,翻來覆去,總也是那麽幾個問題,每天都要背幾遍,像我這麽乏味的人,誰願意跟我聊?那都是交差,我明白。
外形土得掉渣,也硬拽上若幹電視講壇,講壹些相當通俗、相當大眾、相當是人就能聽明白的所謂歷史(類似故事會),當然,該問的還得問下去,該講的可能還得講下去。
這個沒意思。沒意思,也得接著混。
我始終覺得,我是個很平凡的人,扔人堆裏就找不著,放在通緝令上,估計都沒人能記住;到現在還這麽覺得,今天被人記住了,明天就會被人忘記,今天很多人知道,明天就不知道。所以所謂後記,所謂感想,所謂獲獎感言之類的無聊的、亂扯的、自欺欺人的、胡說八道的,都休息吧。
那麽接下來,說點兒有必要說的話。
首先,是感謝,非常之感謝。
記得馬未都同誌有次對我說,這世上很多人都有不喜歡妳的理由。因為妳成名太早,成名太盛,太過年輕,人家不喜歡妳,那是有道理的,所以無論人家怎麽討厭妳、怎麽逗妳,妳都得認,妳該認。
我覺得這句話很有道理,所以壹直以來,我都無所謂。
但讓我感動的是,廣大人民群眾應該還是喜歡我的,壹直以來,我都得到了許多朋友的幫助,沒有妳們,我撐不到今天,謝謝妳們,非常真誠地謝謝妳們。
謝謝。
然後是心得,如果要問我,有個什麽成功心得、處世原則,我覺得,只有壹點,老實做人,勤奮寫書,無他。
幾年來,我每天都寫,沒有壹天敢於疏忽,不惹事,不鬧事,即使所謂盛名之下,我也從未懈怠。有人讓我寫文章推薦商品,推薦什麽就送什麽,還有的希望我做點兒廣告,費用可以到六位數,順手就掙。
我沒有理會。因為我不是商人。
出版商親自算給我聽,由於我堅持把未出版部分免費發表,因此每年帶來的版稅損失,可以達到七位數,這還不包括盜版,以及各種未經許可的文本。
我依然堅持,因為我相信,這是個自由的時代,每個人有看與不看的自由,也有買和不買的自由,任何人都不應該被強迫。
這是我的處世原則,我始終堅持。或許很多人認為這麽幹很吃虧,但結果,相信妳已經看到。
好的,還有歷史,既然寫了歷史,還要說說對歷史的看法。
就剩幾句了,虛的就算了,來點兒實在的吧。
很多人問,為什麽看歷史;很多人回答,以史為鑒。
現在我來告訴妳,以史為鑒,是不可能的。
因為我發現,其實歷史沒有變化,技術變了,衣服變了,飲食變了,這都是外殼,裏面什麽都沒變化,還是幾千年前那壹套,轉來轉去,該犯的錯誤還是要犯,該殺的人還是要殺,嶽飛會死,袁崇煥會死,再過壹千年,還是會死。
所有發生的,是因為它有發生的理由,能超越歷史的人,才叫以史為鑒,然而,我們終究不能超越,因為我們自己的欲望和弱點。
所有的錯誤,我們都知道,然而終究改不掉。
能改的,叫做缺點;不能改的,叫做弱點。
順便說下,能超越歷史的人,還是有的,我們管這種人,叫做聖人。
以上的話,能看懂的,就看懂了,沒看懂的,就當是說瘋話。
最後,說說我自己的想法。
因為看的歷史比較多,所以我這個人比較有歷史感,當然,這是文明的說法,粗點兒講,就是悲觀。
這並非開玩笑,我本人雖然經常幽默幽默,但對很多事情都很悲觀,因為我經常看歷史(就好比很多人看電視劇壹樣),不同的是,我看到的那些古文中,只有悲劇結局,無壹例外。
每壹個人,他的飛黃騰達和他的沒落,對他本人而言,是幾十年,而對我而言,只有幾頁,前壹頁他很牛,後壹頁就了。
王朝也是如此。
真沒意思,沒意思透了。
但我堅持幽默,是因為我明白,無論這個世界有多絕望,妳自己都要充滿希望。
人生並非如某些人所說,很短暫,事實上,有時候,它很漫長,特別是對苦難中的人,漫長得想死。
但我堅持,無論有多絕望,無論有多悲哀,每天早上起來,都要對自己說,這個世界很好、很強大。
這句話,不是在滿懷希望光明時說的,很絕望、很無助、很痛苦、很迷茫的時候,說這句話。
要堅信,妳是壹個勇敢的人。
因為妳還活著,活著,就要繼續前進。
曾經有人問我,妳怎麽了解那麽多妳不應該了解的東西,妳怎麽會有那麽多六七十歲的人才有的感受。我說我不知道。跟我壹起排話劇的田沁鑫導演說,我是上輩子看了太多書,憋屈死了,這輩子來寫。
我沒話說。
還會不會寫?應該會,感覺還能寫,還寫得出來,畢竟還很年輕,離退休尚早,尚能飯。
繼續寫之前,先歇歇,累得慌。
是的,這個世界還是很有趣的。
最後送壹首食指的詩給大家,我所要跟大家講的,大致就在其中了吧。
〖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臺
當灰燼的余煙嘆息著貧困的悲哀
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
用美麗的雪花寫下:相信未來
當我的紫葡萄化為深秋的露水
當我的鮮花依偎在別人的情懷
我依然固執地用凝霜的枯藤
在淒涼的大地上寫下:相信未來
我要用手指那湧向天邊的排浪
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陽的大海
搖曳著曙光那枝溫暖漂亮的筆桿
用孩子的筆體寫下:相信未來
我之所以堅定地相信未來
是我相信未來人們的眼睛
她有撥開歷史風塵的睫毛
她有看透歲月篇章的瞳孔
不管人們對於我們腐爛的皮肉
那些迷途的惆悵、失敗的苦痛
是寄予感動的熱淚、深切的同情
還是給以輕蔑的微笑、辛辣的嘲諷
我堅信人們對於我們的脊骨
那無數次的探索、迷途、失敗和成功
壹定會給予熱情、客觀、公正的評定
是的,我焦急地等待著他們的評定
朋友,堅定地相信未來吧
相信不屈不撓的努力
相信戰勝死亡的年輕
相信未來、熱愛生命〗
二十多歲寫,寫完還是二十多歲,有趣。
是的,這個世界還是很有趣的。
主要參考書目
《明通鑒》,(清)夏燮,中華書局1959年版;
《明季北略》,(清)計六奇,中華書局1984年版;
《明季南略》,(清)計六奇,中華書局1984年版;
《明史》,(清)張廷玉等,中華書局1974年版;
《明會要》,(清)龍文彬,中華書局1956年版;
《明季稗史初編》,(清)留雲居士,上海書店1988年版;
《明史紀事本末》,(清)谷應泰,中華書局1977年版;
《清朝前紀》,孟森,(上海)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;
《明清史講義》,孟森,中華書局1981年版;
《明清史論著集刊》,孟森,中華書局1959年版;
《明史考證》,黃雲眉,中華書局1986年版;
《清初農民起義史料輯錄》,謝國楨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;
《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》,謝國楨,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;
《明實錄》;
《明季黨社考》,[日]小野和子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;
《明代社會生活史》,陳寶良,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;
《玉光劍氣集》,(清)張怡,中華書局2006年版;
《嘉靖以來首輔傳》,(明)王世貞;
《酌中誌》,(明)劉若愚;
《願學集》,(明)鄒元標;
《賜閑堂集》,(明)申時行;
《戚繼光評傳》,範中義,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;
《明文海》,(明)黃宗羲;
《召對錄》,(明)申時行;
《萬歷三大征考》,(明)茅瑞征;
《南明史》,顧誠,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;
《萬歷野獲編》,(明)沈德符,中華書局1959年版;
《明會典》,(明)申時行,中華書局1989年版;
《國榷》,(明)談遷,中華書局2006年版;
《明史簡述》,吳晗,中華書局2005年版;
《南明史》,錢海嶽,中華書局;
《中國斷代史系列——明史(上、下)》,南炳文、湯綱,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;
《晚明史:1573~1644年》,樊樹誌,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;
《劍橋中國明代史》,牟復禮(Frederick W. Mote)、崔瑞德(Denis Twitchett)著;
《南明史》,司徒琳(Lynn H. Struve);
《國史大綱》,錢穆,中華書局;
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》,錢穆,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;
《中國大歷史》,黃仁宇,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;
《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》,黃仁宇,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;
《明清戰爭史略》,孫文良、李誌亭,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;
《馮夢龍全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;
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,(明)顧炎武;
《萬歷起居註》;
《張太嶽先生詩文集》,(明)張居正;
《中國經濟通史》第七卷,吳量愷主編,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;
《崇禎長編》;
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第二卷,譚其驤主編;
《張居正大傳》,朱東潤;
《陳子龍及其時代》,朱東潤;
《清史稿》:《太祖本紀》、《太宗本紀》、《世祖本紀》、《聖祖本紀》、《世宗本紀》、《高宗本紀》、《職官誌》、《食貨誌》、《兵誌》、《地理誌》,及相關列傳;
《明清史論著集刊》、《續編》,孟森,中華書局1984年版、1986年版;
《簡明清史》,戴逸主編,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;
《明清史論著合集》,商鴻逵,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;
《二十五史新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;
《清史新考》,王鍾翰,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;
《明清史新析》,韋慶遠,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;
《明亡清興六十年》,閻崇年,中華書局2006年版;
《袁崇煥傳》,閻崇年,中華書局2005年版;
《楊大洪先生文集》,(明)楊漣;
《三垣筆記》,(明)李清;
《楊文弱先生集》,(明)楊嗣昌。
結束了。
真的結束了嗎?
沒有。
是的,從技術角度講,這篇文章已經結束,我相信,很多人都能看出,它不僅是歷史。
我所述說的,除了歷史,還有很多東西,他們的名字分別叫做:
權力、希望、痛苦、憤怒、猶豫、冷漠、熱情、剛強、軟弱、氣節、度量、孤獨、殘暴、寬恕、忍耐、邪惡、正義、真理、堅持、妥協、善良、忠誠。
足夠多了。
現在我要講述的,是最後壹樣東西,它隱藏在下面的故事裏。
徐宏祖出生的時候,是萬歷十五年。
在這個特定的年份出生,真是緣分。但外面的世界,跟徐宏祖並沒有多大關系,他的老家在江陰,山清水秀,不用搞政治,也不怕被人砍,比較清凈。
當然,清凈歸清凈,在那年頭,要想出人頭地,青史留名,只有壹條路——考試(似乎今天也是)。
徐宏祖不想考試,不想出人頭地,不想青史留名,他只想玩。
按史籍說,是從小就玩,且玩得比較狠、比較特別,不扔沙包,不滾鐵環,只是四處瞎轉悠,遇到山就爬,遇到河就下,人極小,膽子極大。
此外,他極其討厭考試,長大後,讓他去考科舉,死都不去。該情節,放在現在,大致相當於抗拒高考。
這號人,當年跟今天的下場,估計是差不多,被拉回家打壹半死不活,絕無幸免。
然而,徐宏祖的父母沒有打他,非但沒有打他,還告訴他,妳要想玩,就玩吧,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就行。
這種看似驚世駭俗的思想,似乎很不合理,但對徐家人而言,很合理。
對了,應該介紹壹下徐宏祖同誌的家世,雖然他的父母,並非什麽大人物,也沒名氣,但他有壹位祖先,還算是很有名的,當然,不是好名。
在徐宏祖出生前九十年,徐家的壹位先輩進京趕考,路上遇到了壹位同伴,叫做唐寅,又叫唐伯虎。
沒錯,他就是徐經。
後來的事情,之前講過,據說是徐經作弊,結果拉上了唐伯虎,大家壹起完蛋。進士沒考上,連舉人都沒了,所以徐經同誌痛定思痛,對坑害了無數人(主要是他)的科舉制度深惡痛絕,教育子孫,要與這個萬惡的制度決裂,愛考不考,去他娘的。
對這段百年恩怨,徐宏祖是否了解,不清楚,但他會用,那是肯定的。更重要的是,徐家雖說沒有級別,還有點兒錢,所以他決定,索性不考了,出去旅遊。
剛開始,他旅遊的範圍,主要是江浙壹帶,比如紫金山、太湖、普陀山等。後來愈發勇猛,又去了雁蕩山、九華山、黃山、武夷山、廬山等。
但這裏,存在著壹個問題——錢。
旅行家和大俠的區別在於,旅行家是要花錢的,列壹下,大致包括以下費用:交通費、住宿費、導遊費、餐飲費、門票費,如果地方不地道,還有個挨宰費。
我說過,徐家是有錢的,但只是有點兒錢,沒有很多錢,大約也就是個中產階級。按今天的標準,壹年去旅遊壹次,也就夠了,但徐宏祖的旅行日程是:壹年休息壹次。
他除了年底回家照顧父母外,壹年到頭都在外面,但就這麽個搞法,他家竟然還過得去。
原因很簡單,比如交通費,他不坐火車、也不坐汽車(想坐也沒),少數騎馬,多靠步行(騎馬爬山試試)。
住宿費,基本不需要,徐宏祖去的地方,當年大都沒有人去,別說三星級,連孫二娘的黑店都沒有,樹林裏、懸崖上,打個地鋪,也就睡了。
餐飲費,也沒有,我考察過,徐宏祖同誌去的地方,也沒什麽餐館,每次他出發的時候,都是帶著幹糧,而且他很扛餓,據說能扛七八天,至於喝水,山裏面,那都是礦泉水。
門票費也是不用了,當年誰要能在徐宏祖同誌去的地方,設個點收門票,那只能說明,他比徐宏祖還牛,該收。
挨宰費是沒有的,但挨宰是可能的,且比較敞亮,從沒有暗地加價坑錢,都是拿刀,明著來搶。要知道,沒門票的地方,固然沒有奸商,卻很可能有強盜。
據本人考證,徐宏祖最大的花銷,是導遊費用。作為壹個旅行家,徐宏祖很清楚,什麽都能省,這筆錢是不能省的,否則走到半山腰,給妳挖個坑,讓妳鉆個洞,那就休息了。
就這樣,家境並不十分富裕的徐宏祖,穿著儉樸的衣服,沒有隨從,沒有護衛,帶著幹糧,獨自前往名山大川,風餐露宿,不怕吃苦,不怕挨餓,壹年只回壹次家,只為攀登。
從俗世的角度,徐宏祖是個怪人,這人不考功名,不求做官,不成家立業,按很多人的說法,是毀了。
我知道,很多人還會說,這種生活荒謬,是不符合常規的,是不正常的,是缺根弦的,是精神有問題的。
我認為,說這些話的人,是吃飽了,撐的。人只活壹輩子,如何生活,都是自己的事,自己這輩子渾渾噩噩地沒活好,厚著臉皮還來指責別人,有多遠,就去滾多遠。
徐宏祖旅行的唯壹阻力,是他的父母。他的父親去世較早,只剩他的母親無人照料。聖人曾經教導我們:“父母在,不遠遊。”
所以在出發前,徐宏祖總是很猶豫,然而,他的母親找到他,對他說了這樣壹番話:
“男兒誌在四方,當往天地間壹展胸懷!”
就這樣,徐宏祖開始了他偉大的歷程。
他二十歲離家,穿著布衣,沒有政府支持,沒有朋友幫助,獨自壹人,遊歷天下二十余年。他去過的地方,包括湖廣、四川、遼東、西北,簡單地說,大明十三省,全部走遍。
他爬過的山,包括泰山、華山、衡山、嵩山、終南山、峨眉山,簡單地說,妳聽過的,他都去過,妳沒聽過的,他也去過。
此外,黃河、長江、洞庭湖、鄱陽湖、金沙江、漢江,幾乎所有江河湖泊,全部遊歷。
在遊歷的過程中,他曾三次遭遇強盜,被劫去財物,身負刀傷,還由於走進大山,無法找到出路,數次斷糧,幾乎餓死。最懸的壹次,是在西南。
當時,他前往雲貴壹帶。結果走到半路,突然發現交通中斷,住處被當地土著圍困。過了幾天,外面又來了明軍,又開始圍,圍了幾天,就開始打,打了幾天,就開始亂。徐宏祖好歹是見過世面的,跑得快,總算順利脫身。
在旅行的過程中,他還開始記筆記,每天的經歷,他都詳細記錄下來。鑒於他本人除姓名外,還有個號,叫做霞客,所以後來,他的這本筆記,就被稱為《徐霞客遊記》。
崇禎九年(1636),五十歲的徐宏祖決定,再次出遊,這也是他的最後壹次出遊,雖然他自己沒有想到。
正當他考慮出遊方向的時候,壹個和尚找到了他。
這個和尚的法號,叫做靜聞,家住南京。他十分虔誠,非常崇敬雞足山迦葉寺的菩薩,還曾刺破手指,血寫過壹本《法華經》。
雞足山在雲南。
當時的雲南雞足山,算是蠻荒之地,啥也不通,要去,只能走著去。
很明顯,靜聞是個明白人,他知道自己要壹個人去,估計到半路就歇了,必須找壹個同伴。
徐宏祖的名氣,在當時已經很大了,所以他專門找上門來,要跟他壹起走。
對徐宏祖而言,去哪裏,倒是個無所謂的事,就答應了他,兩個人壹起出發了。
他們的路線是這樣的,先從南直隸出發,過湖廣,到廣西,進入四川,最後到達雲貴。
不用到達雲貴,因為到湖廣,就出事了。
走到湖廣湘江(今湖南),沒法走了,兩人坐船準備渡江。
渡到壹半,遇上了強盜。
對徐宏祖而言,從事這種職業的人,他已經遇到好幾次了,但靜聞大師,應該是第壹次。此後的具體細節不太清楚,反正徐宏祖趕跑了強盜,但靜聞在這場風波中受了傷,加上他的體質較弱,剛撐到廣西,就圓寂了。
徐宏祖停了下來,辦理靜聞的後事。
由於路上遭遇強盜,此時,徐宏祖的路費已經不足了,如果繼續往前走,後果難以預料。
所以當地人勸他,放棄前進念頭,回家。
徐宏祖跟靜聞,是素不相識的,說到底,也就是個伴,各有各的想法,靜聞沒打算寫遊記,徐宏祖也沒打算去禮佛,實在沒有什麽交情。而且我還查過,他此前去過雞足山,這次旅行對他而言,並沒有太大的意義。
然而他說,我要繼續前進,去雞足山。
當地人問:為什麽要去。
徐宏祖答:我答應了他,要帶他去雞足山。
可是,他已經去世了。
我帶著他的骨灰去。答應他的事情,我要幫他做到。
徐宏祖出發了,為了壹個逝去者的願望,為了實現自己的承諾,雖然這個逝去者,他並不熟悉。
旅程很艱苦,沒有路費的徐宏祖背著靜聞的骨灰,沒有任何資助,他只能住在荒野,靠野菜幹糧充饑,為了能夠繼續前行,他還當掉了自己所能當掉的東西,只是為了壹個承諾。
就這樣,他按照原定路線,帶著靜聞,翻閱了廣西十萬大山,然後進入四川,越過峨眉山,沿著岷江,到達甘孜松潘。
渡過金沙江,渡過瀾滄江,經過麗江,經過西雙版納,到達雞足山。
在迦葉寺裏,他解開了背上的包裹,拿出了靜聞的骨灰。
到了。
我們到了。
他鄭重地把骨灰埋在了迦葉寺裏,在這裏,他兌現了承諾。
然後,他應該回家了。
但他沒有。
從某個角度講,這是上天對他的恩賜,因為這將是他的最後壹次旅遊,能走多遠,就走多遠吧。
他離開雞足山,又繼續前行,行進半年,翻越了昆侖山,又行進半年,進入藏區,遊歷幾個月後,踏上歸途。
回去沒多久,就病了。
喜歡鍛煉的人,身體應該比較好,天天鍛煉的人(比如運動員),就不壹定好,旅遊也是如此。
估計是長年勞累,徐宏祖終究是病倒了,沒能再次出行。崇禎十四年(1641),病重逝世,年五十四。
他所留下的筆記,據說總共有兩百多萬字,可惜沒有保留下來,剩余的部分,大約幾十萬字,被後人編成《徐霞客遊記》。
在這本書裏,記載了祖國山川的詳細情況,涉及地理、水利、地貌等情況,被譽為十七世紀最偉大的地理學著作,翻譯成幾十國語言,流傳世界。
好的,總結應該出來了,這是壹個偉大的地理學家的故事,他為了研究地理,四處遊歷,為地理學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,是中華民族的驕傲。
是這樣嗎?
不是的。
其實講述這人的故事,只想探討壹個問題,他為何要這樣做。
沒有資助,沒有承認(至少生前沒有),沒有利益,沒有前途,放棄壹切,用壹生的時間,只是為了遊歷?
究竟為了什麽?
我很疑惑,很不解,於是我想起另壹個故事。
新西蘭登山家希拉裏,在登上珠穆朗瑪峰後,經常被記者問壹個問題:
妳為什麽要爬?
他總不回答,於是記者總問,終於有壹次,他答出了壹個讓所有人都無法再問的答案:
因為它(指珠峰),就在那裏!
因為它就在那裏。
其實這個世上很多事,本不需要理由,之所以需要理由,是因為很多人喜歡找抽,抽久了,就需要理由了。
正如徐霞客臨終前,所說的那句話:
“漢代的張騫、唐代的玄奘、元代的耶律楚材,他們都曾遊歷天下,然而,他們都接受了皇帝的命令,受命前往四方。
“我只是個平民,沒有受命,只是穿著布衣,拿著拐杖,穿著草鞋,憑借自己,遊歷天下,故雖死,無憾。”
說完了。
我要講的那樣東西,就在這個故事裏。
我相信,很多人會問,妳講了什麽?
用如此之多的篇幅,講述壹個王朝的興起和衰落,在終結的時候,卻說了這樣壹個故事,妳到底想說什麽?
我重復壹遍,我要講的那樣東西,就在這個故事裏,已經講完了。
所以後面的話,是講給那些不明白的人,明白的人,就不用繼續看。
此前,我講過很多東西,很多興衰起落、很多王侯將相、很多無奈更替、很多風雲變幻,但這件東西,我個人認為,是最重要的。
因為我要告訴妳,所謂千秋霸業,萬古流芳,以及壹切的壹切,只是糞土。先變成糞,再變成土。
現在妳不明白,將來妳會明白,將來不明白,就再等將來,如果壹輩子都不明白,也行。
而最後講述的這件東西,它超越上述的壹切,至少在我看來。
但這件東西,我想了很久,也無法用準確的語言,或是詞句來表達,用最欠揍的話說,是只可意會,不可言傳。
然而,我終究是不欠揍的,在遍閱群書,卻無從開口之後,我終於從壹本不起眼,且無甚價值的讀物上,找到了這句適合的話。
這是壹本臺歷,壹本放在我面前,不知過了多久,卻從未翻過,早已過期的臺歷。
我知道,是上天把這本臺歷放在了我的桌前,它看著幾年來我每天的努力,始終的堅持,它靜靜地、耐心地等待著終結。
它等待著,在即將結束的那壹天,我將翻開這本陪伴我始終,卻始終未曾翻開的臺歷,在上面,有著最後的答案。
我翻開了它,在這本臺歷上,寫著壹句連名人是誰都沒說明白的名人名言。
是的,這就是我想說的,這就是我想通過徐霞客所表達的,足以藐視所有王侯將相,最完美的結束語:
〖成功只有壹個——按照自己的方式,去度過人生。〗
後記
本來沒想寫,但還是寫壹個吧,畢竟那麽多字都寫了。
記得前段時間,去央視《面對面》接受訪談,主持人問我,書寫完的時候,妳有什麽感覺?
其實這個問題,我曾經問過我自己很多次,高興、興奮、沮喪,什麽都有可能。
但當這刻來到的時候,我只感覺沒有感覺。
不是矯情。
怎麽說呢,因為我始終覺得寫這玩意兒,是個小得沒法再小的事。然而,很快有人告訴我,妳的書在暢銷排行榜蹲了幾天、幾月、幾年,然後是幾十萬冊、幾百萬冊,直到某天,某位仁兄很是激動地對我說,改革開放三十年,這本書的發行量,可以排進前十五名。
有意思嗎?說實話,有點兒意思。
雷打不動的還有媒體——報紙、電視臺,從時尚到社會,從休閑到時局,從中央到地方,從中國到外國,借用某位同誌的話,連寵物雜誌都上門找妳。平均壹天幾個訪問,問的問題,也大致雷同,翻來覆去,總也是那麽幾個問題,每天都要背幾遍,像我這麽乏味的人,誰願意跟我聊?那都是交差,我明白。
外形土得掉渣,也硬拽上若幹電視講壇,講壹些相當通俗、相當大眾、相當是人就能聽明白的所謂歷史(類似故事會),當然,該問的還得問下去,該講的可能還得講下去。
這個沒意思。沒意思,也得接著混。
我始終覺得,我是個很平凡的人,扔人堆裏就找不著,放在通緝令上,估計都沒人能記住;到現在還這麽覺得,今天被人記住了,明天就會被人忘記,今天很多人知道,明天就不知道。所以所謂後記,所謂感想,所謂獲獎感言之類的無聊的、亂扯的、自欺欺人的、胡說八道的,都休息吧。
那麽接下來,說點兒有必要說的話。
首先,是感謝,非常之感謝。
記得馬未都同誌有次對我說,這世上很多人都有不喜歡妳的理由。因為妳成名太早,成名太盛,太過年輕,人家不喜歡妳,那是有道理的,所以無論人家怎麽討厭妳、怎麽逗妳,妳都得認,妳該認。
我覺得這句話很有道理,所以壹直以來,我都無所謂。
但讓我感動的是,廣大人民群眾應該還是喜歡我的,壹直以來,我都得到了許多朋友的幫助,沒有妳們,我撐不到今天,謝謝妳們,非常真誠地謝謝妳們。
謝謝。
然後是心得,如果要問我,有個什麽成功心得、處世原則,我覺得,只有壹點,老實做人,勤奮寫書,無他。
幾年來,我每天都寫,沒有壹天敢於疏忽,不惹事,不鬧事,即使所謂盛名之下,我也從未懈怠。有人讓我寫文章推薦商品,推薦什麽就送什麽,還有的希望我做點兒廣告,費用可以到六位數,順手就掙。
我沒有理會。因為我不是商人。
出版商親自算給我聽,由於我堅持把未出版部分免費發表,因此每年帶來的版稅損失,可以達到七位數,這還不包括盜版,以及各種未經許可的文本。
我依然堅持,因為我相信,這是個自由的時代,每個人有看與不看的自由,也有買和不買的自由,任何人都不應該被強迫。
這是我的處世原則,我始終堅持。或許很多人認為這麽幹很吃虧,但結果,相信妳已經看到。
好的,還有歷史,既然寫了歷史,還要說說對歷史的看法。
就剩幾句了,虛的就算了,來點兒實在的吧。
很多人問,為什麽看歷史;很多人回答,以史為鑒。
現在我來告訴妳,以史為鑒,是不可能的。
因為我發現,其實歷史沒有變化,技術變了,衣服變了,飲食變了,這都是外殼,裏面什麽都沒變化,還是幾千年前那壹套,轉來轉去,該犯的錯誤還是要犯,該殺的人還是要殺,嶽飛會死,袁崇煥會死,再過壹千年,還是會死。
所有發生的,是因為它有發生的理由,能超越歷史的人,才叫以史為鑒,然而,我們終究不能超越,因為我們自己的欲望和弱點。
所有的錯誤,我們都知道,然而終究改不掉。
能改的,叫做缺點;不能改的,叫做弱點。
順便說下,能超越歷史的人,還是有的,我們管這種人,叫做聖人。
以上的話,能看懂的,就看懂了,沒看懂的,就當是說瘋話。
最後,說說我自己的想法。
因為看的歷史比較多,所以我這個人比較有歷史感,當然,這是文明的說法,粗點兒講,就是悲觀。
這並非開玩笑,我本人雖然經常幽默幽默,但對很多事情都很悲觀,因為我經常看歷史(就好比很多人看電視劇壹樣),不同的是,我看到的那些古文中,只有悲劇結局,無壹例外。
每壹個人,他的飛黃騰達和他的沒落,對他本人而言,是幾十年,而對我而言,只有幾頁,前壹頁他很牛,後壹頁就了。
王朝也是如此。
真沒意思,沒意思透了。
但我堅持幽默,是因為我明白,無論這個世界有多絕望,妳自己都要充滿希望。
人生並非如某些人所說,很短暫,事實上,有時候,它很漫長,特別是對苦難中的人,漫長得想死。
但我堅持,無論有多絕望,無論有多悲哀,每天早上起來,都要對自己說,這個世界很好、很強大。
這句話,不是在滿懷希望光明時說的,很絕望、很無助、很痛苦、很迷茫的時候,說這句話。
要堅信,妳是壹個勇敢的人。
因為妳還活著,活著,就要繼續前進。
曾經有人問我,妳怎麽了解那麽多妳不應該了解的東西,妳怎麽會有那麽多六七十歲的人才有的感受。我說我不知道。跟我壹起排話劇的田沁鑫導演說,我是上輩子看了太多書,憋屈死了,這輩子來寫。
我沒話說。
還會不會寫?應該會,感覺還能寫,還寫得出來,畢竟還很年輕,離退休尚早,尚能飯。
繼續寫之前,先歇歇,累得慌。
是的,這個世界還是很有趣的。
最後送壹首食指的詩給大家,我所要跟大家講的,大致就在其中了吧。
〖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臺
當灰燼的余煙嘆息著貧困的悲哀
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
用美麗的雪花寫下:相信未來
當我的紫葡萄化為深秋的露水
當我的鮮花依偎在別人的情懷
我依然固執地用凝霜的枯藤
在淒涼的大地上寫下:相信未來
我要用手指那湧向天邊的排浪
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陽的大海
搖曳著曙光那枝溫暖漂亮的筆桿
用孩子的筆體寫下:相信未來
我之所以堅定地相信未來
是我相信未來人們的眼睛
她有撥開歷史風塵的睫毛
她有看透歲月篇章的瞳孔
不管人們對於我們腐爛的皮肉
那些迷途的惆悵、失敗的苦痛
是寄予感動的熱淚、深切的同情
還是給以輕蔑的微笑、辛辣的嘲諷
我堅信人們對於我們的脊骨
那無數次的探索、迷途、失敗和成功
壹定會給予熱情、客觀、公正的評定
是的,我焦急地等待著他們的評定
朋友,堅定地相信未來吧
相信不屈不撓的努力
相信戰勝死亡的年輕
相信未來、熱愛生命〗
二十多歲寫,寫完還是二十多歲,有趣。
是的,這個世界還是很有趣的。
主要參考書目
《明通鑒》,(清)夏燮,中華書局1959年版;
《明季北略》,(清)計六奇,中華書局1984年版;
《明季南略》,(清)計六奇,中華書局1984年版;
《明史》,(清)張廷玉等,中華書局1974年版;
《明會要》,(清)龍文彬,中華書局1956年版;
《明季稗史初編》,(清)留雲居士,上海書店1988年版;
《明史紀事本末》,(清)谷應泰,中華書局1977年版;
《清朝前紀》,孟森,(上海)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;
《明清史講義》,孟森,中華書局1981年版;
《明清史論著集刊》,孟森,中華書局1959年版;
《明史考證》,黃雲眉,中華書局1986年版;
《清初農民起義史料輯錄》,謝國楨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;
《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》,謝國楨,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;
《明實錄》;
《明季黨社考》,[日]小野和子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;
《明代社會生活史》,陳寶良,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;
《玉光劍氣集》,(清)張怡,中華書局2006年版;
《嘉靖以來首輔傳》,(明)王世貞;
《酌中誌》,(明)劉若愚;
《願學集》,(明)鄒元標;
《賜閑堂集》,(明)申時行;
《戚繼光評傳》,範中義,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;
《明文海》,(明)黃宗羲;
《召對錄》,(明)申時行;
《萬歷三大征考》,(明)茅瑞征;
《南明史》,顧誠,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;
《萬歷野獲編》,(明)沈德符,中華書局1959年版;
《明會典》,(明)申時行,中華書局1989年版;
《國榷》,(明)談遷,中華書局2006年版;
《明史簡述》,吳晗,中華書局2005年版;
《南明史》,錢海嶽,中華書局;
《中國斷代史系列——明史(上、下)》,南炳文、湯綱,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;
《晚明史:1573~1644年》,樊樹誌,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;
《劍橋中國明代史》,牟復禮(Frederick W. Mote)、崔瑞德(Denis Twitchett)著;
《南明史》,司徒琳(Lynn H. Struve);
《國史大綱》,錢穆,中華書局;
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》,錢穆,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;
《中國大歷史》,黃仁宇,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;
《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》,黃仁宇,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;
《明清戰爭史略》,孫文良、李誌亭,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;
《馮夢龍全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;
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,(明)顧炎武;
《萬歷起居註》;
《張太嶽先生詩文集》,(明)張居正;
《中國經濟通史》第七卷,吳量愷主編,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;
《崇禎長編》;
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第二卷,譚其驤主編;
《張居正大傳》,朱東潤;
《陳子龍及其時代》,朱東潤;
《清史稿》:《太祖本紀》、《太宗本紀》、《世祖本紀》、《聖祖本紀》、《世宗本紀》、《高宗本紀》、《職官誌》、《食貨誌》、《兵誌》、《地理誌》,及相關列傳;
《明清史論著集刊》、《續編》,孟森,中華書局1984年版、1986年版;
《簡明清史》,戴逸主編,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;
《明清史論著合集》,商鴻逵,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;
《二十五史新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;
《清史新考》,王鍾翰,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;
《明清史新析》,韋慶遠,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;
《明亡清興六十年》,閻崇年,中華書局2006年版;
《袁崇煥傳》,閻崇年,中華書局2005年版;
《楊大洪先生文集》,(明)楊漣;
《三垣筆記》,(明)李清;
《楊文弱先生集》,(明)楊嗣昌。